閱讀《余英時談話錄》筆記
(全民專欄/陳天授)2021年11月,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余英時口述、李懷宇整理的《余英時談話錄》。我筆記了下列幾項重點:
一、余英時與新儒家關係。余英時指出:我寫了〈錢穆與新儒家〉一文,另外有一個重要原因,錢先生逝世以後,很多人把錢先生寫入新儒家的一員。但是,錢先生跟唐如此不合,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四先生一九五八年簽名的〈中國文化宣言〉,錢先生不肯簽名。這是錢夫人鄭重請我寫的。(《余英時談話錄》,頁55)
殷海光得癌症的時候,他的論敵徐復觀托金耀基把三千塊錢送給他。徐復觀這一點很好,雖然是思想上的論敵,互相罵得一塌糊塗,這個時候表示同情,很有義氣。(《余英時談話錄》,頁175)
1950年代開始,新亞書院辦新亞講座,請各種人來演講。後來徐復觀從蔣介石那兒拿到錢,辦《民主評論》,那算是香港一個重要的媒體。(《余英時談話錄》,頁181)
1970年代余英時在新亞書院校長期間,在《明報月刊》發表一篇談自由的文章,引發羅孚領導的《新晚報》的批判,說余英時回香港來不為中美關係著想,還批評文化大革命。羅孚後來託徐復觀給余英時轉話:對不起,他剛好去大陸,批評余英時的文章是他手下編輯把這東西發表了。(《余英時談話錄》,頁182-3)
二、余英時的胡適「充分世界化」觀。胡適與第二代新儒家的熊十力三位海外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基本上沒有甚麼直接交鋒。這是胡適自一九五八年回台定居以後很少發表批評中國文化的言論,只有在台中農學院和英文”Social Changes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兩次演講中重提「纏足」的老話,但與二十世紀二O、三O年代文章的刺激性已不能相提並論。何況這兩次演講並不是針對新儒家而發。至於新儒家對胡適的攻擊,也只有徐復觀一人屢屢行之文字,唐君毅、牟宗三則只有私下議論。與第二代新儒家對壘的不是胡適本人,而是「接著胡適講」的一群「文化激進派」,最初以殷海光為主將,以《自由中國》雜誌為基地,後來又由《文星雜誌》的一群更年輕的作者繼承下來〔按:指的是李敖等〕。這些人只是「接著」而不是「照著」胡適講的,他們痛詆中國文化、提倡「全盤西化」,在當時很有影響,但不應由胡適負責。(《余英時談話錄》,頁258)
徐復觀痛罵胡適並不是單獨上陣,與他並肩作戰的人多得很。事實上,如果以文化保守主義與文化激進主義為劃界,則前者才是二十世紀五、六O年的主流,具有深厚的政治與社會基礎,後者則處於邊緣地位,成為被打壓的對象。一九六O年代起,《自由中國》被封閉,雷震入獄,殷海光被台大解職,受監視與軟禁,其他遭株連而死或囚者不可勝數。胡適在中央研究院內連一個「文化激進」的同志也沒有。……我算來算去,胡適在台灣學術界的追隨著僅剩下毛子水一人。毛子水在一九五O年代初曾與徐復觀一度發生過「義理」與「考證」的爭論,但很快便為人所遺忘。毛子水極少寫文章,也不是「激進派」,更無權勢可言,他沒有任何「打壓」新儒家的力量。……《自由中國》潰滅以後,新儒家安然無恙,《民主評論》也照常出版。從比較廣闊的政治、社會背景上看,究竟誰是「主流」,誰是「邊緣」,恐怕也是一個仍待爭論的問題。(《余英時談話錄》,頁260-1)
胡適與「全盤西化」,我認為有必要澄清「全盤西化」的問題。胡適雖然一度附和陳序經的「全盤西化」 的口號,但是三個月之內便發現這是一個誤導的名詞,所以特意寫了〈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一文,正式拋棄了這一口號,而代之以「充分世界化」。他說「充分」不過是「儘量」或「用全力」的意思。他的「世界化」當然主要是指科學與民主而言。但是這二者雖是西方發展出來的,在中國卻已為文化保守主義者接受,……胡適更明白承認:「況且西洋文化確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願採取,事實上也決不會全盤採取。」把胡適早已鄭重宣布拋棄的「全盤西化」四個字繼續扣在他頭上,痛加咒罵,這是批胡的人的一貫策略,他們根本對他的公開修正視若無睹。(《余英時談話錄》,頁263-4)
余英時與新儒家思想的爭論,除了學術思想上的因素之外,其中還糾葛胡適自由主義與國民黨蔣介石政權,錢穆當年進北大教書的受遇於胡適,還有錢穆創辦新亞書院與時任台灣省教育廳長陳雪屏(余英時岳父)的居間協助。在「兩蔣時代」的1968年、1974年,錢穆、余英時師生分別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等等錯綜複雜因素,亦是研究余英時與新儒家思想關注的焦點。
三、余英時提倡「知識人」的重視「人的尊嚴」。余英時的史學雖延續近代中國新漢學的「乾嘉考證」之風,但有其超越新漢學「實證」科學之處。余一方面受胡適五四啟蒙運動的影響,關心民主、科學的課題,同時在他史學的風格上,呈現了錢穆與陳寅恪將史學與時代結合的論題選擇,余英時可謂現代型的公共知識分子。
《余英時談話錄》指出:「知識人」這個名詞是我現在提倡的。……2002年正式提出來的。以後我就盡可能用知識人,而不用知識分子。……從前「知識分子」是一個中性的名詞,後來就變質了。我是受陳原的影響,日本人也用知識人,講政治人、經濟人、文化人都可以,為什麼不能用知識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因為語言是影響很大的東西,語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語言,就是鼓動暴力。(《余英時談話錄》,頁226)
余英時的「知識人」是強調對「人的尊嚴」的取代「知識分子」一詞。周言在《余英時傳》指出:「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余英時傳》,頁415)。
1980年代余英時頻繁就兩岸問題發聲,尤其是「六四事件」,1990年代余英時有「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之感嘆,並開始不定期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固定就「公共事務」議題發聲,成為了解余英時晚年政治立場,政治思想的一個視窗。
美國就1970年代起,將原本以政府作為主體的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教育,參考企業管理(business administration)的議題導向與跨域整合,形成了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s)領域。從為因應社會經濟發展與變遷的觀點,凸顯當前「公共事務」的重視「社會主義式」議題,似可比之於「企業管理」的「資本主義式」實際運作模式。
四、余英時主張「傳統與現代化」的取徑模式。余英時指出:我認為中國的傳統價值裡面也有「普世價值」,例如自由、寬容、民主、科學、人權。我常常說,中國沒有人權這兩個字,但是有人權的想法。而且有些中國已經有的東西與西方一配合,就從原來的傳統進入現代化了。現代化就是把已經有的價值用現代的語言與方式跟其他文化中的東西聯合起來,講成同樣的東西,不覺得生硬和冒昧。(《余英時談話錄》,頁315)
我們可以說余英時的學術思想是結合錢穆對中國文化執著,與胡適對西方實證科學優點的融合而成的一家之言。余英時秉性謙沖為懷的並不希望像新儒家在思想文化傳承,有所謂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派別。余英時有如業師錢穆的不立門戶,可是從現在余英時思想受到學界有如「胡適學」的崇敬,對於當前華人世界的影響已蔚成一股「余英時學」熱潮,余英時的為學與處世總會讓人有一股「如沐春風」的感受,其影響力的深遠是擋不住的。
五、余英時認為中華文化轉機在日常實踐。余英時指出:在香港中文大學兩年,使我對歷史的看法不是那麼天真。我覺得理論沒有那麼重要了。研究歷史不是光靠理論,要知道人的複雜性。……光是在書房裡念書,永遠看不到人性的深處。(《余英時談話錄》,頁60-61)
余英時在中文大學改制風波,給他帶來很深的感觸,認為「光是在書房裡念書,永遠看不到人性的深處」。所以他對於新儒家太講形上學,卻忽略了日常實踐,是不能為中華文化帶來轉機,也不能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對現實也無能為力。用現在的話:狹義的新儒家提倡的道統是很抽象,而且是不接地氣的。
六、余英時對於政治「遙遠的興趣」。關於余英時與第三勢力關係,或余英時與自由派知識人關係的研究,可以從余英時父親余協中、岳父陳雪屏等家族人與國民黨蔣介石之間的互動;或如余英時與胡適、王世杰等自由主義者之間的關係。
黃克武在《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書中,引1959年3月4-5日的《蔣介石日記》謂:包圍陳誠的「小宵政客」之一是陳雪屏,蔣對陳雪屏最不滿的地方即是他勾結胡適,「陳雪屏為反動分子包蔽,並藉胡適來脅制本黨,此人積惡已深,其卑劣言行再不可恕諒」、「昨晡以陳雪屏卑劣行動直等於漢奸不能忍受,再三自制幸未暴怒氣也」。(《胡適的頓挫》,頁377-385)
之後,陳雪屏在1959月5月19日國民黨八屆二中全會選舉中常委時就落選了。這是一段蔣介石對陳雪屏與陳誠、胡適走得太近的記載?蔣氏父子認為陳誠在拉攏北大知識分子而結黨結派。陳雪屏曾書「正須謀獨往,何睱計群飛」一幅墨寶,影射當年陳誠與蔣經國兩方陣營,在政治上的不甚投契。後來陳雪屏雖然淡出中華民國政治圈,但1990年在李登輝總統任內仍受聘總統府資政。最後,在台灣終老,葬在台灣。
周言《余英時傳》中特別提到:余先生當時還談到了他家庭的一些情況,……當然還有一些敏感話題我沒有談,心想以後如果余先生提到可以順便問一下,比如說台灣島內對他曾和蔣經國之間的關係曾有過非議,諸如此類,但是礙於情面,我終究沒有問過這些問題,我想這些問題談起來既深且長,三言兩語無法概括,這其中的關係,並不是余先生那一本《民主與兩岸動向》的書可以簡單解釋的。(《余英時傳》,頁459)
余英時過世後,周言出版了《余英時傳》一書,其中第二十五章〈時代的風陵渡口〉,特別提到「從六四事件到中國學社/中國學社的台前幕後/中國學社的內部紛爭」,是針對余英時於「六四事件」之後,有關在普林斯頓大學成立「中國學社」、「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及後來與馬樹禮主持下「台灣三民主義大同盟」之間的關係與運作情形如何?做進一步分析。
七、余英時「中國情懷」與「台灣本土化」思維。余英時指出:東晉的元帝是創始的皇帝,當時的口號就是「王與馬,共天下」,非靠王家不可,要不然站不住的。因為皇帝是從北方來的,像大陸人跑到台灣,沒有本地人靠不住,所以必須本土化。本土化的過程中,南方的士族很重要(《余英時談話錄》頁282)
這本土化議題,從政權本土化的本質,延伸「蔣經國在台灣的本土化政策」,和提倡自由民主的不廢儒家文化,延伸「新儒家徐復觀激進文化的本土化論述」,正如羅爾斯(John Rawls)在《政治自由主義》中指出,在民主與自由的時代,仍需要有一個背景文化。
余英時認為:現代儒學必須放棄全面安排人生秩序的想法,然後儒學才真能開始它的現代使命,而明清儒學所開啟的「日用常行化」或「人倫日用化」觀點。依此,如果從「文化即日常生活實踐」的文化資源創新轉化,當前台灣產業界流行的文化創意產業,中華文化和儒家文化其在中華民台灣發展的未來性如何?余英時有「當代胡適」之譽,胡適與余英時的文化資產可有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可能性?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
八、感想。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曾是在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學生的王汎森教授,曾引龔自珍的一首詩,說和余英時先生交往是「萬人叢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周言《余英時傳》,頁455)。我就借用這句話,作為閱讀《余英時談話錄》的心得與感想。(作者現任台北城市大學榮譽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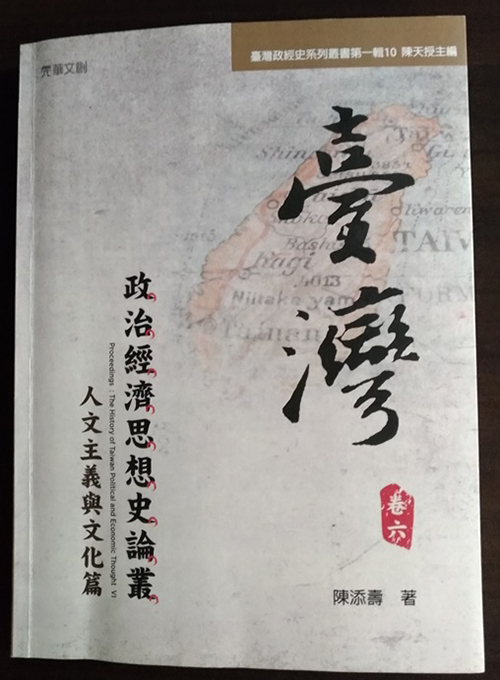
- 綜合新聞-04-19- 113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專業輔導人員目睹家暴輔
- 課程活動-04-19- 最後倒數階段 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培訓營報名至
- 頭版新聞-04-19- 體育署全額補助短期失能理賠差額 保障職業運動
- 全民專欄-04-19- 〔安齋三談70〕我的臺灣近代資本主義史論
- 企業報導-04-19- 華視「健康最前線」:引領健康新潮流,共創美
- 綜合新聞-04-18- 紐西蘭訪團金山泡湯 台紐原住民傳統歌舞文化
- 綜合新聞-04-18- 福和橋主梁遭車輛撞擊毀損 即日起緊急封閉部
- 綜合新聞-04-18- 2024新北鐵道馬拉松4/21熱鬧開跑 周邊道路交管全
- 綜合新聞-04-18- 新北濕地藝術季將開跑 創作補助金兩萬五千元
- 社會新聞-04-18- 新北水土保持巡迴講習 23日新莊農會登場

 紐西蘭訪團金山泡
紐西蘭訪團金山泡 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白雲出岫香江情—
白雲出岫香江情— 開啟人生魔法找回
開啟人生魔法找回 樹林環保河濱公園
樹林環保河濱公園 白雲堂藝術硏究會
白雲堂藝術硏究會 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昭庚:中醫養生‧
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昭庚:中醫養生‧ 洪鈞培文教基金會祕書長洪惠博士:
洪鈞培文教基金會祕書長洪惠博士: 黃禎憲皮膚科診所院長黃禎憲:皮膚
黃禎憲皮膚科診所院長黃禎憲:皮膚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名譽教授林哲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名譽教授林哲 洪鈞培文教基金會祕書長洪惠博士:
洪鈞培文教基金會祕書長洪惠博士: 洪鈞培文教基金會祕書長洪惠博士:
洪鈞培文教基金會祕書長洪惠博士: 不會講話也能吵!萌娃
不會講話也能吵!萌娃 「打臉版小蘋果」瘋傳
「打臉版小蘋果」瘋傳 性感女神 Mikiyo
性感女神 Mikiyo 莊舒涵 Quxy
莊舒涵 Quxy YouTube
YouTube